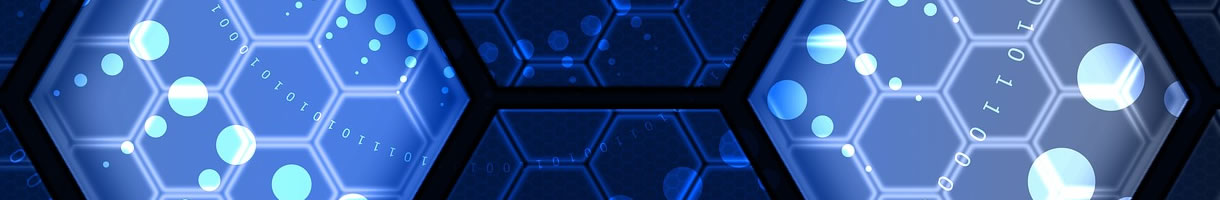日本“宪政之父”的野望:全面征服中国,实际上轻而易举?
甲午战争时,日本社会弥漫着狂热的战争情绪,出版界也涌现大量评论中国的书籍,内容极尽诋毁与蔑视之能事。
击败清朝之后,这种仇视、蔑视型的“中国观”由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又进一步泛滥和沉淀,并深深植入日本民众心中,几乎成为信条。
在这些“蔑华”著述当中,以尾崎行雄撰写的《中国处分案》最具代表性。那么问题来了,尾崎行雄究竟是“何方神圣”?《中国处分案》一书当中主要都说了些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尾崎行雄(1858—1954),号咢堂,早年就学于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先后担任《新潟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的记者与主笔。
1882年参与创建立宪改进党,1890年首次议会选举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00年参与组建立宪政友会,历任东京市长、文部大臣、司法大臣、国会参议员,连续25次当选众议员,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父”。
作为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尾崎行雄在“大正护宪运动”中冲锋陷阵,与犬养毅一起被誉为“宪政之神”;大正与昭和时期,他反对向西伯利亚出兵,主张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同时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进行了不懈斗争。

但在明治时代(1868—1912),尾崎行雄虽然对内主张民主政治,但对外尤其是对华却是有名的强硬论者。
1884年12月4日,朝鲜爆发了带有“联日排清,脱离中国独立”色彩,旨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甲申政变。
不久,《邮便报知新闻》先后刊登了《须知中国朝鲜之地位远在日本之下》《国际法不承认中国与朝鲜》《勿使中国朝鲜增长倨傲心》等多篇由尾崎行雄执笔的社论。可以说,敌视、蔑视中国的态度,从这一时期就现出端倪了。
1895年1月,尾崎行雄的《中国处分案》在博文馆出版,他在序言中就将“不仁不义”等负面字眼,一股脑地扣在了中国的头上:
日清战争的是“文野之战”,是“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秩序与混乱、慈爱与暴虐、进步与保守、自由与压抑、立宪与专制、交通与锁攘之战”;日清两国的胜败,将极大地导致文明的消长、道义的兴废、贸易的盛衰、陆海军备的变更”。
这本《中国处分案》,合计由“东亚之长计”、“中国之命运”、“列国的对清政略”、“帝国的对清政略”、“北京城下之盟约”、“占领之难易”、“列国的交涉”、“占领的利害”、“他日的机会”、“帝国的天职”等十章构成。
在“中国的命运”一章中,尾崎行雄从“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中国人的政治思想”、“中国人的道德”、“中国人的战斗力”、“历朝的命数”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对于“中国人的国家思想”,他在书中指出: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朝廷即等同于国家,首都即代表着朝廷。因此,一旦首都陷落,朝廷便随之崩塌;而朝廷的崩塌,即被视为国家的灭亡。
因此,他的结论是:
国家思想、忠义心、爱国心、团结力,皆为保国之要素,中国人无一具备,这样的情况要在这倾夺的世界保持独立,未知有也。
关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
中国人虽然富有文学思维,却普遍缺乏真正的政治思想。那些看似高明的奏议论策,本质上不过是文学创作,辞藻华丽却脱离实际。
历代名臣奏议大多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即便偶有所谓的“政治思想”,也往往是谋取私利的算计。官场行为腐败至极,中国人从未体验过欧美社会那种清正严明的政治生态。
在中国,官吏贪腐受贿被视为常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自古就缺乏保障。所以,这样的民族,无疑是难以在当今世界独立自强。

关于“中国人的道德”,
中国人不仅缺乏政治道德,也缺失基本的社会公德。自古便言行脱节,典籍所载的教条往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对于中国人而言,学习文化反而成为修炼虚伪的手段。因此读书越多,权谋诈术往往越深。这导致中国人身上长期存在虚妄、狡诈、无耻、无操守、不义、缺乏魄力、惯于欺瞒等负面特质。一个这样的民族,又如何能立足于现代文明世界?答曰:不可,断然不可!”
对于“中国人的战斗力”,
中国人崇尚文治而非武力,追求实利而非征战。中国官兵使用的武器,本质上并非杀戮工具,更多是威慑的象征。正如我曾将中国的“战”字解读为“旗鼓的竞赛”那般,虽带调侃,却贴近本质。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战争胜负取决于军容声势:鼓声震天、旌旗蔽日者为胜,旗鼓不足者为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声势的较量,是军容之战,而非常规的武器之战。
对于清军羸弱的战斗力,他表示:
尽管近代中国开始引进欧美武器,战争形态发生突变,但一个两千八百年来习惯以旗鼓竞赛定胜负、崇文好利的民族,难以在短期内掌握真正的战争逻辑。因此战场上常见士卒阵亡则将领溃逃,将领受伤则全军瓦解的局面。

最终,尾崎行雄认为:
中国人的战斗力今后只能长期处于水平线之下,这样的民族也能在如今争夺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吗?曰:不能,断然不能!
简言之,在他看来,中国只能承受亡国的惨淡结局,“且其灭亡已迫在眉睫。”
值得一提的是,尾崎行雄一直强烈反对“日中同盟论”。原因很简单,“与一个注定灭亡的国家结盟,如同搀扶垂死的病人上战场,对日本有百害而无一利。”
不过话说回来,他话锋一转,旋即指出,“中国虽已丧失自保能力,但倘若能够获得外部支持,或可延缓崩溃进程”。他从地缘、种族及东亚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主张日本应该以“东亚引领者”的身份,主动“扶助”中国。
当然,“扶助”存在着一个大前提,即“中国必须将军事、外交及财政(维持这些职能所必需)的主导权交予日本”,否则中国将“无可救药”;作为交换,“日本负责为中国彻底消除上述导致灭亡的根源”,
但这样一来,“中国非纯然的独立国家了”。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煞有介事地宣称,只有这种选择,才能带来“中国民族之幸福”、“人类之庆事”。原因很简单:
对于中国人民,我实怀有不忍弃之不顾之心。因此,日本理应代行天命,统领其疆域、治理其民众,旨在将文明之光普照中华四百余州。
若我大日本能取得中国主权,派遣大量官吏执掌其内政与外交等关键职位,推动军政改革,重整纲纪、确立军制,便足以维护内外安定,保全疆土与民生。
若由中国人自行推行改革,犹如等待黄河水清,百年难成;但若由我帝国臣民主导经营,不出二十年必使其面貌焕然一新。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之福祉吗?难道不是人类文明之幸事吗?

如何才能“让中国驯服于日本的主宰”呢?对此,尾崎行雄认为,当务之急是占领北京,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不攻占敌国首都就撤退,是军队的耻辱。因此我军必须彻底挽回颜面,一举拿下北京,才能彰显军威。
第二,如果想彻底震慑中国人,单靠一时威慑远远不够——一旦和平重现,他们骨子里的傲慢迟早会复苏,甚至再度挑衅。而展现我军实力的最佳方式,就是攻克他们的京城。
第三,中国人善变狡黠,天下无双。所以如果不先掐住要害再谈和议,他们必定施展拖字诀,诡计百出,最终让谈判陷入僵局。
第四,若不给予足够深刻的教训,无论签订什么盟约,清人都绝不会真心遵守。而占领北京,正是从精神上重击他们的关键一招。
第五,中国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一再证明:攻陷首都,国家便告灭亡。因此要真正惩罚中国人,占领北京显得尤为必要。
第六,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壮举,至今仍激励着国人,其感召力堪比万卷经典。我军一旦占领北京,哪怕千年之后,也足以唤醒颓丧之人奋起拼搏。

一言概之,在尾崎行雄看来:
纵然在其它战场百战百胜,若不攻入北京,仍无法击垮中国人顽固执拗的气焰。可以说,任何和谈都必须以占领北京为前提。只有清朝彻底交出主权,完全听命于日本,才能算作真正的降服。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是否可以完全征服中国呢?对此,尾崎行雄结合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从历史上看,他将中国人视为一个“奴性十足、甘当亡国奴”的民族:
纵观历史,凡试图经略中国者,无论起于内部或来自外邦,皆面临同一困境:无人具备足以横扫天下四百州的充足兵力、军械与资金。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奇特现象——它似乎总会为占领者提供征服自己所需的资源!
这个国家甚至习惯于为占领者承担占领费用。更确切地说,它有一种"自费请人来占领"的根深蒂固的习性。以我国兵马之精良、资金之雄厚,若仍不能占领如此邦国,岂非不合常理?
其居民素来缺乏独立卫国的意识,历史上虽未受外族人统治,但他国占领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因为中国人历来甘愿接受许多被视为野蛮异族的统御,他们将朝廷视作暂居的旅店,无论谁来占领,只要能让其安居乐业,便心满意足。
爱新觉罗氏强令汉人变更衣冠发式,以丑态为美,而民众竟能安然接受,这不正是明证吗?被迫改变服饰发式,本是愚昧至极之举;强行推行,自是统治者的粗暴无谋。然而中国人却坦然服从且不以为耻,甚至头拖长辫而洋洋自得。普天之下,再没有像中国这样易于征服、易于统治的民族了。

那么问题来了,现实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呢?
尾崎行雄认为,尽管中国的人口与疆域远超日本十倍有余,但“征服的难易程度取决于统治的凝聚力——疆域过大反而难以统筹,而中国正是因其庞大,反而更易被征服”:
由于中国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导致“海军与陆军体系支离破碎,各自为政,脉络不通。直隶军队惨败,两湖地区的军队却无动于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甚至暗中讥讽”。
纵观战事至今,可以说“日本并非与中国整体作战,而只是在与直隶一省交锋”。唯有随着战线扩大,才可能真正称之为与“中国”——或更准确地说,与东部沿海数省——之间的战争。
正因为中国兵民处于分裂状态,才能“驱使东部军队征讨西部,率领北部民众攻打南部”。中国今日之局面,恰恰正是如此。
最终,尾崎行雄得出结论: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若要全面占领中国,其行事自应与叛逆、流寇、蛮族首领有着本质区别。帝国不能在所有事务上都依赖被占领方的供给,诸如经费与兵力必须由我方自行承担。
然而,这仅是在实施占领前期的必要准备。一旦完成占领,即便我不去强行征敛,彼也必将主动提供兵马、经费等一切所需。我国虽已备妥二十万精兵与三亿军费,却可能几无使用之必要。即便一时投入,不久也必能全数收回。

鉴于尾崎行雄的《中国处分案》成书于日军连战连捷、清廷败局已定的背景之下,因此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者的自负与傲慢,以及对战败方的极度蔑视。
他与福泽谕吉一样,主张对待近邻“恶友”就应如欧美列强般冷酷无情。鉴于这类论调与当时日本国民的亢奋情绪高度契合,因而流传甚广。
进入20世纪30年代,尾崎行雄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反对军部,同时对军国主义思想的扩张与国家的法西斯化倾向深感不满。
1941年,他公开致信时任首相东条英机,明确反对旨在强化军部控制的“翼赞选举”议员推荐制度,此举使他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中陷入孤立。
1942年,他因发表支持议员田川大吉郎的演说,被当局指控犯有“不敬罪”并遭到起诉,但最终获判无罪。

对于明治时代的“中国观”,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如下自白: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爆发,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实现了长达十年的夙愿,内心感到无比欣慰。所有的一切,要追溯到明治十七年(1884年)。
当时,中法两国因安南(越南)问题爆发冲突,我正担任《邮便报知新闻》的记者,以特派通讯员身份前往上海。那时的日本社会,一方面盛行崇拜中国的风气,另一方面也对西洋充满追捧,我对这两种盲目崇拜都十分反感。恰逢中法交战,我认为这是一个观察双方实力的难得机会。
在动身之前,我专门向多位长居中国或曾深入中国内地的“中国通”当面请教。然而抵达上海实地考察后,却发现许多情况与那些前辈的描述并不相符。
起初,我怀疑是自己判断有误——毕竟那些前辈在中国生活多年,经验丰富。但经过反复核实,我愈发确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才是真实的。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审视并修正了对中国的认知。

初到上海,我便目睹了中国军队出征前的混乱景象:年过七旬的老将军身后竟跟着两三台妻妾的轿子,士兵们人人背着雨伞、手提灯笼,还携带着数不清的旌旗锣鼓。场面之荒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即便是我这个外行,也一眼看穿中国根本毫无战斗力可言。
从那一刻起,我强烈意识到:必须通过一场战争挫败中国的傲慢气焰。于是,我开始公开主张“征伐中国论”。这正好是日清战争爆发的十年前。
整整十年间,我不断呼吁讨伐中国,甚至被世人视作疯子。直到日清战争真正打响,人们才明白我并非狂言。
然而,当时日本朝野上下仍深受四五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影响,即便在开战之初也意外地心存畏惧;而中国方面却始终轻视日本,视之为落后小邦。战端一开,果然如我所料,我国陆海军连战连捷,势如破竹。此刻我的心情,唯有"难以言表的痛快"可以形容!

一言概之,这次上海之行已经让尾崎行雄充分意识到,清朝纲纪败坏、道德腐败、民族分裂,必定走向灭亡。至于清朝之所以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没有灭亡”,无外乎是因为西方列强不了解清朝真相之故。
正如尾崎行雄所料,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彻底看清了这个昔日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腐朽与衰弱。于是,他们彻底卸下了戒心,妄图肢解和瓜分中国。
日本各界也普遍认为,中国已不再是“竞争对手,也没有资格成为平等对待的伙伴,充其量只是一个缺乏主体性的征服对象而已。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府的“扩张胃口”越来越大——在给全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现如今,“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更何况,“日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
不过话说回来,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当知识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