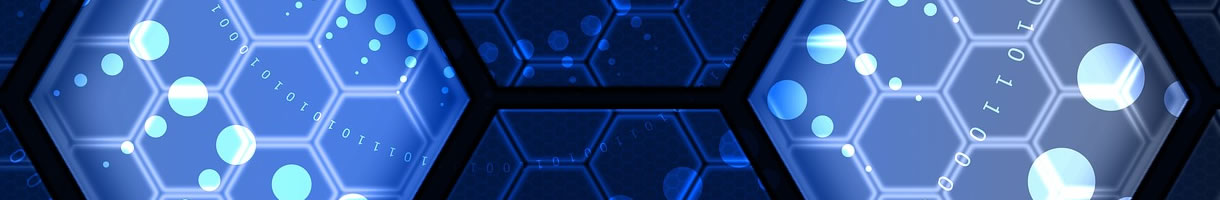历史的终局:为何中国工业霸权必将取代美国金融霸权?
引言:历史的循环与霸权的本质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全球霸权的更迭并非偶然,而是遵循着深刻的经济与科技规律。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是,那些曾凭借金融和贸易主导全球的“金融霸主”,其辉煌往往昙花一现,最终会被以强大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霸主”所取代。这一规律背后蕴含着一个核心论点:国家霸权的根本来源在于其创造财富和力量的实体经济基础。金融霸权,作为一种“寄生性”的霸权形式,其繁荣往往建立在对既有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之上,并以牺牲实体经济的长期发展为代价,最终因基础的空心化而走向衰落。工业霸权则截然不同,它建立在能够不断创造新财富、推动生产力飞跃的强大实体生产之上,因此具有更强的内生韧性和扩张潜力。
历史的镜像——从荷兰到英国的霸权更迭
17世纪,荷兰凭借其强大的商业贸易网络和创新的现代金融制度,开创了一个“黄金时代”,成为欧洲“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当时,荷兰的商船总载货量高达400万吨,一度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总和。阿姆斯特丹成为全球贸易的商业中枢和金融中心,其创设的股票交易所和商业规则至今仍在影响世界。这种繁荣的根基,在于其对全球商贸的垄断和对金融工具的有效运用。然而,在这辉煌成就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隐患:其实体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到了18世纪,荷兰的经济已深度金融化,制造业竞争力严重不足。其引以为傲的造船业被英国超越。面对来自英国的竞争,荷兰政府曾试图通过征收最高40%的关税和推行保护政策来应对,但由于制造业长期缺乏竞争力,这些政治手段最终未能扭转其霸权的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于,资本的逐利本能驱使荷兰人将两百多年来积累的巨额资本,借贷给英、法等国的政府与企业,以享受稳定丰厚的利息收入,而非投资于冒险艰难的实业生产。这种资本的“脱实向虚”导致了国家实业的萎缩,也使得政府为维持表面的繁荣而不断举债,到1713年,债务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以上。与此同时,荷兰的军事力量因军备废弛而日渐衰弱。这与其竞争对手英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自1649年起便开始制定改进和扩大海军的计划,并在短短三年内将舰船规模扩大了两倍。英国成立了专门的海军委员会,将国家安全、经济增长与海军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中央政府统一协调、以工业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建设,最终在1780年至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将过度金融化、军备废弛的荷兰彻底击垮。蒸汽动力和铁路运输的出现,使得英国工业化商品远比荷兰的转运商品更具价格优势。在强大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支持下,英国全面接管了全球航线,最终终结了荷兰的金融霸权。荷兰的霸权之殇清晰地揭示了金融繁荣脱离实体工业基础的脆弱性,以及在生产力革命面前,旧有霸权模式的迅速崩塌。

英国的崛起完美地印证了工业霸权战胜金融霸权的规律。英国凭借率先点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火种,在以纺织、煤炭和钢铁为核心的产业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到1850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全球的39%,贸易占36%,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这种工业生产力上的飞跃,是其取代荷兰、奠定全球霸权的基础。然而,历史的周期律似乎并未放过英国。到了19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开始重蹈荷兰的覆辙,资本从实业领域逐步转向金融领域。工业革命积累的巨额财富大量流入债券、保险、海外贷款和殖民地项目,而对制造业的投资却不再是重点。伦敦金融城迅速崛起为全球资金中枢,到1880年代,英国的对外投资已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资本输出国。到1900年,伦敦每10位富人中,就有7人是依靠海外股息与债息生活,而非经营工厂。这一转变催生出一个以金融收益为生的“绅士阶层”,标志着英国正式迈入金融帝国时代。这种过度金融化最终削弱了英国的实体经济基础和创新能力。在以重工业、电气和化工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逐渐落后于德国和美国等新兴工业强国。美国凭借其技术创新,经济规模在1872年便超过了英国,并在1894年工业产值登顶世界第一。虽然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并未像英荷战争那样通过直接的军事冲突完成,而是看似“和平”地发生,但这仅仅是表象。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而美国则凭借其无可争议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实力,成为战后重建世界的“建筑师”。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总部纷纷设在纽约和华盛顿,而非伦敦,这标志着全球霸权的彻底转移。英国的衰落模式再次完美地复刻了荷兰的路径,证明了霸权之巅的资本终将因逐利而“脱实向虚”,最终导致其霸权的衰落。
霸权更迭的核心逻辑:生产力与权力
历史经验揭示,霸权更迭的根本驱动力是生产力范式的转变。工业革命的本质是一场“效率革命”,它使人类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能力。一个国家只要率先实现生产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并将其大规模产业化,就能迅速提升其经济规模和贸易份额,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生产力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它还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石。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现代军事力量的根本保障。它能够为军事提供充足的物资、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持续的研发投入。例如,英国工业革命使其能够大规模建造以钢铁和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这种科技与工业的结合赋予了其强大的军事控制力,成为其维持全球霸权的支柱之一。此外,工业霸主还能够通过其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将自己的技术标准和商业规则推广至全球,进而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生产力优势是国家权力最直接的来源,也是霸权得以维系的核心。

当一个国家登顶霸权之巅,其经济结构往往会发生深刻转变。资本的逐利本能会驱使其从回报周期长、利润率低的实体生产转向回报快、利润高的金融投机。这种“脱实向虚”的机制使得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被切断。金融业的收益不再主要来源于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是通过发行金融衍生品、信贷膨胀和资产交易等方式“以虚生虚”。这种过度金融化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其表现为产业空心化、债务膨胀和资产泡沫。金融业虽然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但其所产生的财富在本质上是实体经济财富的二次分配,而非真正的创造。这种“寄生性”使得整个经济基础变得脆弱。此外,金融化模式也削弱了国家的长期创新能力。当资本可以在金融领域轻易获得暴利时,企业将缺乏动力进行周期长、风险高但对国家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研发和工业创新。更深层次的内在矛盾体现在“特里芬悖论”上。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发行国,金融霸主获得了铸币税和“薅羊毛”的特权。但为了满足全球对该货币的流动性需求,其必须长期维持贸易逆差和巨额债务。这使得经济陷入一种“借新钱还旧钱”的脆弱循环,最终使金融霸权成为一个“空壳”。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衡量工业霸权的标志已超越了单纯的产值规模。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尤其是对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和核心技术环节的垄断,已成为新的标准。美国的“去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主动进行战略调整的结果,即将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包,而自身专注于“微笑曲线”的高端环节。这表明,新的工业霸权不仅要能生产,更要能控制。然而,这种模式也存在内在风险。虽然美国在制造业的知识密集型高端部分仍保持领先,但其对海外生产的过度依赖,使得一些关键的供应链面临更大的全球风险,也加剧了其经济的脆弱性。这凸显出,在霸权更迭的博弈中,对全球供应链的掌控权已成为工业实力竞争的核心焦点。
当代博弈:中美竞争的维度与未来走向
当前,美国正处于其金融霸权的巅峰,但其经济结构也表现出历史性金融霸主所共有的特征与挑战。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超过21%,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财富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经济模式使得美国的GDP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市的表现,而非实体经济的真实产出。正如研究所示,从1947年到2012年,美国金融业的增加值增长了212倍,而制造业仅增长了30倍。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美国经济对金融武器产生“路径依赖”,加剧了其债务负担和经济脆弱性。面对日益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政府正积极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以试图扭转局面。然而,该战略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高昂的劳动力成本、老旧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昂的工厂建设成本。虽然美国在军事和金融领域的控制力为其霸权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但其背后的产业空心化和巨额债务问题(截至2024年底,经常账户赤字达1.13万亿美元,占GDP的3.9%)正构成其霸权的内生脆弱性。美国试图通过制造业回流来重塑其工业基础,但其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高昂的生产成本和固化的经济结构正在构成巨大的内在阻力。

与美国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正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基础和战略性科技投入,展现出新工业霸权崛起的雏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已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超过51万家。这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强大的产业韧性。在科技创新方面,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资未来。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量超过3.6万亿元,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投入强度达到2.68%。中国在《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已升至第11位,是近10年来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中国正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新能源汽车等前沿领域取得突破。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2024年产量达1316.8万辆,连续10年居全球首位。此外,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5G网络和移动物联网网络,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些“新基建”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中国的崛起模式与历史上的工业霸主高度相似:拥有庞大的实体工业基础,持续且巨大的研发投入,以及能够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国家战略。其“军民融合”战略更是将工业生产力直接转化为军事实力,这与当年英国建立“海军委员会”的逻辑如出一辙。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而不仅仅是低端生产环节。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场由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引发的新工业革命浪潮中。这场革命并未颠覆“生产力是霸权之源”这一核心逻辑。相反,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将技术创新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并加速了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核心已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转向“技术政治”。数据、算法和算力已成为新的战略资源和国家权力的“倍增器”。谁能掌握这些要素,谁就拥有了技术霸权,进而能影响国际权力分配。美国作为人工智能的发源地,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高端芯片和人才规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中国则凭借其海量数据、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强大的算力基础设施等天然优势,在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领域走在前面。这场竞争的焦点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对技术标准制定权和“数字主权”的争夺。未来的霸权形式可能不再是单一的“金融”或“工业”霸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融合实体工业、数字技术和金融体系的“数字-工业复合型霸权”。然而,历史规律并未失效。新科技革命只会加速霸权更迭的进程,因为那些能够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强大工业生产力、并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国家,将最终胜出。
结论与展望
历史周期律清晰地表明,金融霸权的内在脆弱性决定了其无法持久。霸权的根基始终在于其创造财富的实体工业生产力。历史上的荷兰和英国都因过度金融化而削弱了这一根基,最终被新兴的工业强国所取代。
当前,中美竞争的本质,正是美国“金融帝国”模式与中国“工业巨人”模式的博弈。虽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金融霸权维持着全球主导地位,但其产业空心化、债务危机和基础设施老化等内在矛盾日益凸显。中国则凭借其作为“世界工厂”的强大工业基础、对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投入以及在“新基建”领域的领先地位,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并未颠覆这一历史规律,反而可能加速和强化它。未来的霸权竞争将围绕着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展开,谁能赢得这场新工业革命的领导权,谁就将掌握未来的霸权。真正的胜利者将是那些能够将技术创新转化为强大工业生产力、并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国家。